男女主角分别是徐建平热门的其他类型小说《我的名字,叫张兰英。全局》,由网络作家“大概一只面包”所著,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,本站纯净无弹窗,精彩内容欢迎阅读!小说详情介绍:我鼻子骂我没规矩。我低头不敢吭声,再也不敢提。我以为日子就这样了:等着,过着,熬着。可东北那人带来的消息,像把火,“哗啦”一下烧掉了我心里最后一点模糊的指望,也烧出了一股不顾一切的劲儿。我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,我得去问清楚。留留已经四个多月了,可以断奶了。可她太黏我,嘴一离开就哇哇哭,哭到小脸通红。我心疼得肝胆都要碎了,眼泪止不住地往心里流,可这个奶,必须得断。第二天一早,趁婆婆还没起,我悄悄去找了个尖头红辣椒,掰开捣碎,只闻着味儿就呛人。那个味道冲得我眼睛发酸。像烟味。太太以前抽烟,独自一人的时候,一口一口,望着窗外。当时我觉得烟味难闻,现在想或许是她扛日子的法子。用热水泡了一小碗。抱着留留,哄住她,狠着心蘸了点辣椒水,轻轻抹在自己...
《我的名字,叫张兰英。全局》精彩片段
我鼻子骂我没规矩。
我低头不敢吭声,再也不敢提。
我以为日子就这样了:等着,过着,熬着。
可东北那人带来的消息,像把火,“哗啦”一下烧掉了我心里最后一点模糊的指望,也烧出了一股不顾一切的劲儿。
我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,我得去问清楚。
留留已经四个多月了,可以断奶了。
可她太黏我,嘴一离开就哇哇哭,哭到小脸通红。
我心疼得肝胆都要碎了,眼泪止不住地往心里流,可这个奶,必须得断。
第二天一早,趁婆婆还没起,我悄悄去找了个尖头红辣椒,掰开捣碎,只闻着味儿就呛人。
那个味道冲得我眼睛发酸。
像烟味。
太太以前抽烟,独自一人的时候,一口一口,望着窗外。
当时我觉得烟味难闻,现在想或许是她扛日子的法子。
用热水泡了一小碗。
抱着留留,哄住她,狠着心蘸了点辣椒水,轻轻抹在自己胸口。
喂米汤时,婆婆过来,问:“怎么不喝奶?”
我说:“留留拉肚子,大概奶水太浓了。”
她看了我一眼,没说话。
下午抱她吃奶,她一口咬下去,立刻皱起小脸,缩回来,嘴一张就哇哇大哭。
婆婆听见进来,问:“又怎么了?”
我哄着说可能要长牙,不想吃。
她盯着我胸口看了一会,眼神复杂,什么也没问就出去了。
留留哭得厉害,抓着我衣襟不放。
我一边轻拍她背,一边往她嘴里喂熬稀的米汤。
她哭着哭着,终于开始大口大口地喝米汤。
那一刻,我心像被人使劲攥了一把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晚上她还是哭了几回,又睡了几回。
我就坐在床沿看她,一边熬夜一边准备自己的包袱。
东拼西凑攒下的几张粮票,婆婆说留着冬天换棉花的十块钱,我统统收好贴身放着,感觉像是偷了天大的东西。
太太留给我的那块红头巾,我找出来,叠进去又拿出来,又重新叠了一遍,它是这趟浑浊婚姻里,唯一一点属于我的、体面的东西。
我不知道东北那么远的地方怎么走,不知道车票要多少钱。
但我知道县里有车站,有北上的火车,只要人到了车站,总归能想办法出去。
第二天,婆婆在院子里晒酱菜,我去搭把手。
她重重叹了口气,把笸箩一扔看着我说:“你这几天怪不对劲的,整天
东翻西找,还急吼吼地给孩子断奶。”
她停了一下,语气变得更硬,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:“心思活络也要掂量掂量自己。
你个不识字的文盲,出去了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,也没有出路的。”
我心底猛地被刺了一下,但脸上没露出来,没正面应她,只说:“太太以前的老亲戚托我带点草药过去,我去跑一趟,顺便看看能不能换点米回来。”
她“哼”了一声,没有再问。
可我走开的时候,感觉到她往我背后看了一眼,那眼神里,有怀疑,有担忧,也有那种“我就看着你能折腾出什么”的看好戏一样的东西。
夜里我没睡着,只觉得心咚咚跳得厉害。
等天刚蒙蒙亮,鸡叫第一声,我轻手轻脚把包袱背上,弯腰抱起还在睡的留留。
她睡得正香,呼吸浅浅的,小身子贴着我胸口软软的。
我在她额头亲了一口,又小心地把她放回去,盖好被角。
她像是感应到了,迷迷糊糊哼了一声,小手往外伸了伸,抓了个空。
我蹲下来,在她耳边轻声说:“姆妈去问清楚就回来。”
门是我轻手轻脚关上的,怕吵醒婆婆。
我在门口站了一会,没有听到留留醒来的哭声。
天快亮了,我看着出村的路,深吸了口气。
不管识得几个字,不都一样是人吗?
3火车站比我想的更乱更吵。
人挤着人,声压着声,汗味、烟味混在一起,直往鼻子里钻。
我在售票口前站了半天,晕头转向,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。
兜里揣着那几张揉得发软的粮票和那十块钱,手心都出汗了。
身边一拨一拨人往前挤,有人扯着嗓子骂人,有人扯着嗓子喊小孩。
我的身子本来就单薄,被人挤得左晃右晃,好几次差点摔倒,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。
售票员在窗口后头,脸藏在阴影里,只大声冲外面吼:“要问的站到前头来问!”
我鼓起勇气,好不容易挤到窗口前,张嘴问:“去东北,要怎么买?”
她头也不抬,一边撕票一边飞快地说:“去东北啊?
你得先坐到青岛,换船,从青岛上船到大连,再转车往里走。
东北那么大,你问我要卖哪儿的票?”
我张着嘴,脑子一片空白,哑了半天,只能问:“那……去青岛多少钱?”
她眼皮都没抬一下,冰冷地报了个价:“
。
我揣着那张地址,找到厂区行政大楼的方向。
我要去查户籍表,查职工名册。
我要看到的不是照片上的“沈兰”,而是她到底有没有资格站在那里。
我要看到的,是我到底有没有名分。
6厂里管档案的女职工,姓杜。
五十多岁,说话细声细气,眼角都是笑纹。
她原先不肯管,怕惹事。
直到我说:“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,婚书也有,只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还在纸上。”
她看了我半晌,说:“今天谁都不在,你自己翻吧。”
她手指一动,指了个方向。
我咽了口口水,艰难开口:我,不识字。
能麻烦您帮我翻吗?
我把剩下的粮票塞给她。
她叹了口气,替我翻到那一页,指着配偶栏问我:自己的名字认识吗?
认识。
沈兰的名字不在户籍上。
她不是配偶,不是母亲,只是被贴在红榜上的“临时演员”。
而我是登记了的张兰英,是他不敢提起的那一栏。
我手里的那张纸,写着我的名字,蓝字清楚,盖着章。
这就够了。
我没去敲门。
我只是来确认:我不是他口中的“老家那个”。
我回去了。
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第二天早上,我坐上了回乡的火车。
留留还在等我。
可我知道,她不会没有娘。
她的姆妈,走过千里,拿回了一张纸。
在这张没人会看的纸上写着我的名字。
写得清清楚楚,盖着章,不容否认。
我是徐建平的妻子。
我也是徐留留的母亲。
7回程没像去的时候那样害怕。
铁轨响的时候,我靠着车窗睡了好几觉,没梦。
梦的事,都在现实里过完了。
门没插,推开就是冷风一扑。
留留听到响动,从床上哼了一声,爬都不会,还是挣着朝我这边翻。
我一把把她抱起来,她就笑了,嘴里喊:“啊、啊、啊。”
她认得我。
婆婆抬头看了一眼,“你回来了。”
然后又低下头继续剥葱,“菜篮在灶台边上,去拿。”
她把那张纸拿出来,在炕头放下。
婆婆扫一眼,眼里那点子防备、嘴上的冷嘲,全都没了。
她什么也没说,转身进了屋。
从那之后,她再没提“文盲”这两个字。
村里冬天比以往更冷。
柴不够,盐也不够。
不知道算不算庆幸,家里只有三个女的。
不用眼巴巴的等着工分换粮。
跟“你是谁”不明白比起来,
那么多干啥。”
现在她却乐呵呵地挨家挨户通知:“我孙女考上大学咯,留留是有出息的,咱徐家有大学生了。”
我没拆穿她,按她的意思摆了席,热热闹闹吃了一下午。
徐建平没回来。
我给他写过信,告诉他留留考上了,让他抽空回来看看,哪怕说一句“恭喜”。
他回信说:“恭喜。
‘他’今年落榜,明年再考,我这边得照看着。
留留既然考上县里,不如直接到市里来吧,我这边人脉广,能给她安排更好的学校和前程。
你在老家看好妈就行,外面的事女人操心不来。”
那个“他”,就是他跟沈兰那个“儿子”。
他把全部心思给了另一个孩子,却从没问留留读的是什么,在哪儿读,要带多少东西,要多少钱学费。
他以为他现在随口一句“让她过来”,就能抹掉过去这么多年他的缺席和我们吃的苦?
就能轻而易举地“接手”我靠命拼出来的留留的未来?
用他的“人脉”来“安排”?
他甚至还想用这种方式把我永远钉死在老家!
我没生气。
我不意外。
他的事,我早看透了。
他以为用一张纸,用几个钱,用几句轻飘飘的话,就能掌控一切,把我打发了。
幸好,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不识字的张兰英了。
走那天,村口的班车一早就来了。
我扛着铺盖,留留背着书包,我们娘俩并肩往站牌走。
婆婆追出门,给了我包糕点和手绢包起来的几十块钱。
嘴里念叨着:“省着点吃,也……别饿着自己。”
我接过来,说了声:“嗯。”
上车的时候,留留抢着把我拉上去,说:“姆妈,你得陪我认路。”
我笑:“嗯,陪你认。”
我偷偷报了学校旁边食堂的帮工名额,打饭、擦桌子、抄菜谱,换两顿饱饭,换一个能离她近点的地方。
我不读书,但我能守着她读完。
我坐在车尾,看她坐在窗边翻录取通知书,阳光照在她头发上,每一根都在发光,发亮。
(番外)我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。
从有记忆起,我就跟着“太太”生活。
她是大户人家出身的女人,家道中落后,一个人搬到了我们村子边上住。
村里人都叫她“太太”,我也跟着这么喊。
一开始大家对她指指点点,说什么“资本家小姐落难”之类的风凉话。
可
力气问了一句:“是她带着孩子,还是……他们一起有的?”
那人更支吾了,脸涨得通红,说不清。
他挠了挠头,眼睛不敢看我:“反正厂里人都当他们是一家子过日子……也没人敢问太细。”
他说的每一个字,都像风雪天的冰雹,挡不住地让人发寒。
手里的粥碗“啪”地一声掉在地上,米汤溅得到处都是,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烫。
屋里明明烧着火,我却觉得从里到外都透着凉意。
2我没再说一个字,只觉得脚底都打飘。
留留刚睡着,小嘴微微张合,还在梦里小口小口地吃奶。
婆婆跟着进来,看着我,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我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,只低声,一字一句地说:“反正,村里都是认我的。”
我这辈子,像是一场被定好的戏。
十八岁,懵懵懂懂,像被交易一样,村里长辈领着我上了徐家的门。
听说这门亲事还是以前收养我的太太生前给我定好的。
她是个从前大户人家出身的女人,搬到村边住,大家都叫她“太太”。
她不让学认字,说女人识太多字没好处,字是规矩,规矩多了,命就不安分,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。
婆婆知道我没念过书愣了下,很快就摆摆手,说进了老徐家,好好当媳妇、传宗接代就行。
新婚夜,徐建平,我的丈夫,戴着眼镜,斯斯文文的模样,却从头到尾黑着脸,一副不情愿的样子。
他比我大三岁,只冷冷地说:“以后别直呼我名,没规矩。”
又说:“你不识字没关系,听话就行。”
不到半个月,他就收拾行李走了,说是回东北粮站上班。
我问他是不是不过了?
他闭着眼,像在说梦话:“回厂。
你在这儿过你的。”
婆婆拍着大腿数落他,他却不耐烦地回:“是您让我娶的。
事办完了,剩下的您自己看着办。
我得走了,厂里离不开人。”
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后来婆婆总说:“读书人脾气就是倔。
等你给他生个儿子就好了。”
家里就剩两个女人。
我守着几亩地和几只鸡,从早到晚地干活。
他一年才回来一次,每次待不了几天就走得急。
有一年他走后连信都没留,婆婆说收着了,我晚上偷偷翻她箱子,摸出那封信,是写给她的,说今年不回来了。
第二天婆婆发现,指着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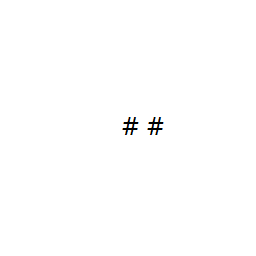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